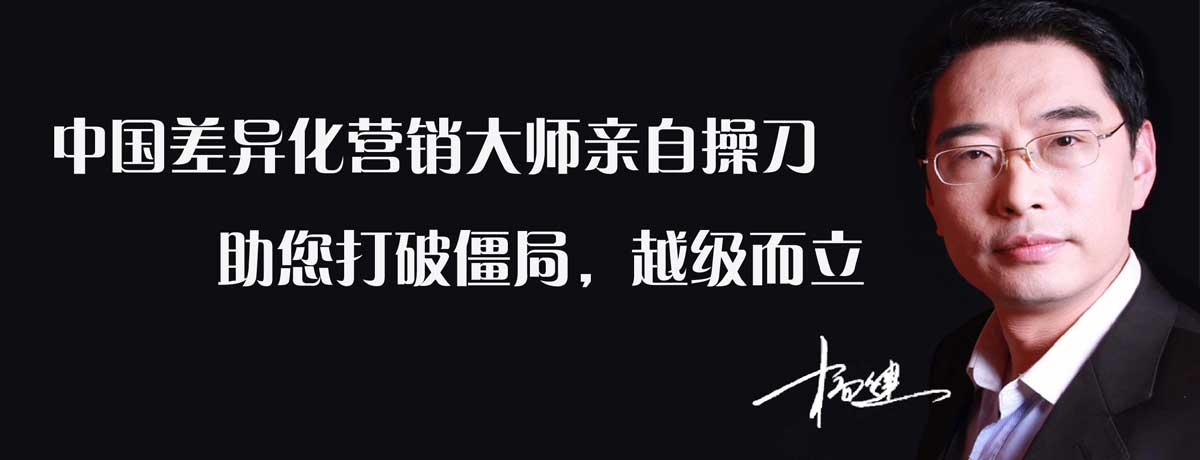韦伯论权力的类型
“统治”应该叫做在一个可能标明的人的群体里,让具体的(或者:一切的)命令得到服从的机会。因此,不是任何形式的对别人实施“权力”和“影响”的机会。这个意义上的统治(“权威”),在具体的情况下,可能建立在服从的极为不同的动机之上:从模糊的习以为常,直至纯粹目的合乎理性的考虑:任何一种真正的统治关系都包含着一种特定的最低限度的服从愿望,即从服从中获取(外在的和内在的)利益。
并非任何统治都利用经济手段。更不是任何统治都有经济目的。然而,任何对于很多人的统治,一般(不总是绝对必要)都需要有一班人,也就是说,需要有(一般来说)可靠的机会,让一些可以标明的、可靠地服从的人,采取旨在特意为执行统治的一般法令和具体命令的行动。行政管理班子对统治者(或统治者们)的服从,可能纯粹出自习俗,或者纯粹由于情绪,或者受到物质利害关系,或者受到思想动机(价值合乎理性)所约束。这类动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统治的类型。在这里,在统治者和行政管理班子之间的结合,出自纯粹物质的和目的合乎理性的动机,就意味着像通常那样,结合的持久性比较起来不稳定。一般还有其他的--情绪的或者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在非日常的情况下,可能惟有这些动机是决定性的。在日常生活中,习俗,除此而外,物质的即目的合乎理性的利益,主宰着统治者和行政管理班子的关系以及其他的关系。然而,习俗或利害关系,如同结合的纯粹情绪的动机或纯粹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一样,不可能构成一个统治的可靠的基础。除了这些因素外,一般还要加上加一个因素:对合法性的信仰。
一切经验表明,没有任何一种自愿地满足于仅仅以物质的动机或者仅仅以情绪为动机,或者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勿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但是,根据所要求的合法性种类的不同,服从的类型,为保证服从而确定的行政管理班子的类型,以及实施统治的特点,也是根本不同的。因而它们的影响也是根本不同的。因此,根据它们典型的合法性要求来区分统治的种类是恰当的。而且从现代的,即众所周知的情况谈起,也是适当的。
1.选择这个区分的出发点,而不是选择任何一个别的区分的出发点,这样做是否有道理,只能看是否卓有成效。某些其他典型的区分标志暂时搁置起来,以后再作补充,大概不致于会有重大的弊端。一种统治的“合法性”--哪怕仅仅因为它同财产占有的合法性在着非常肯定的关系--,就具有一种绝不是仅仅在“思想方面的”意义。
2.并非任何一种惯例或法律保障的“权益要求”,都应该叫做一种统治关系。否则,劳动者在其工资权益要求的范围内就会成为雇主的“主子”,因为应司法法官的要求,必须提供给他使用这种要求。事实上,他在形式上是一位“有权”接受支付的权益要求的交换伙伴。与此相反,由形式上自由的契约产生和权益,当然并不排除一种统治关系的概念:例如,在劳工制度和指令里宣布雇主对劳动者的统治,采邑领主对自由进入采邑关系的领主封臣的统治。依仗军事纪律的服从,形式上是“非自愿的”,依仗车间纪律的服从,形式上是“自愿的”,这丝毫改变不了车间纪律也是服从一种统治的事实。官员职位也是通过契约被接受的,也是可以辞职的,甚至“臣仆”关系也可能被自愿接受的,并且也是可以解除的(受到某些限制)。绝对的不自愿只存在于奴隶的身上。
诚然,在另一方面,仅仅是一种由垄断地位所制约的经济“权力”,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把交换条件“强加”于交换伙伴的可能性,本身也不叫做是一种“统治”,正如某种其他的诸如由性爱方面的,或者体育方面的,或者在讨论方面的或者其他方面的优势所制约的“影响”,不能叫做“统治”一样。如果一家大银行有能力把一种“支付条件同盟”强加于其他银行,这也还不应该叫做“统治”,只要还没有建立一种直接的顺从关系,使那个银行领导的指令可以要求和有机会纯粹作为指令得到尊重,并检查其执行情况。当然,在这里如同在其他各处的情况一样,过渡的界限是模糊的:从债务义务到债务奴役有着形形色色的中间阶段。一个“沙龙”的地位可能十分险要,直至接近一种权威的权力地位的边缘,却并非必然是“统治”。在现实中,严格的区分往往是不可能的,不过正因如此,明确的概念就更加必要。
3.当然,一种统治的“合法性”,也只能被看作是在相当程度上为此保持和得到实际对待的机会。这远不是说,对一种统治的任何顺从,首先(或者哪怕是仅仅往往)以这种合法性的信仰为取向。顺从可能是个人或整个群体纯粹出自机会主义的原因,是一种虚情假意的奉承,也可能出自自己的物质利益而实际上言听计从,也可能由于个人的软弱和束手无策,不可避免地加以忍受。然而,这不是对一种统治分类的准则,而是:它的固有合法性要求按其种类在相当程度上
“适用”,巩固它的持久存在,并参与决定所选择的统治手段的种类。此外,一种统治可能--而且在实际上往往这样--由于统治者和他的行政管理班子(警卫、古罗马禁卫军、“赤”卫队或者“白”卫军),对待被统治者的明显的共同利益和被统治者的毫无防卫能力,而得到绝对的保障,以致它本身可能鄙夷这种对合法性的要求。于是,根据他们之间存在的权威基础的方式,统治者和行政管理班子之间的合法性关系的方式,也是十分不同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构成统治
结构的准则,这一点将要进一步论述。
4.“服从”应该意味着,服从者的行为基本上是这样进行的,即仿佛他为了执行命令,把命令的内容变为他的举止的准则,而且仅仅是由于形式上的服从关系,而不考虑自己对命令本身的价值或无价值有什么看法。
5.纯粹从心理学家上看,这种命令和服从的因果链条看起来是不同的,尤其是:服从可能出于“直觉”,或者出于“移情”。但是,在这里,这种区分不能应用于统治的类型的构成上。
6.统治对社会关系和文化现象影响的领域,比起初看起来要广泛得多。例如,在学校里实行的统治,深深地打上正统适用的语言和书写形式的烙印。政治上自主的团体的方言,即它们的统治者把它作为公文体语言的方言,变成了这种正统的语言和书写的形式,并且导致了“民族的”分开(例如荷兰同德国分开)。然而,父母的统治和学校的统治,远远超过那些(而且仅仅是表面上的)形式上的文化成果的影响,给青年、因而也是给人们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7.一个团体的领导者和行政管理班子,形式上作为统治者的“公仆”出现,还丝毫不能证明违背作为“统治”的性质。关于所谓的“民主”在实质上的事实情况,以后将作单独论述。但是,在几乎任何可以设想的情况下,都必须赋予它们以某种最低程度的权威性的命令权力,也就是说,在这个意义上是“统治”的权力。
合法统治有3种纯粹的类型。它们的合法性的适用可能首先具有下列性质:
1.合理的性质:建立在相信统治者的章程所规定的制度和指令权利的合法性之上,他们是合法授命进行统治的(合法型的统治);
2.传统的性质:建立在一般的相信历来适用的传统的神圣性和由传统授命实施权威的统治者的合法性之上(传统型的统治);
3.魅力的性质:[建立在]非凡的献身于一个人以及由他默示和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者英雄气概,或者楷模样板之上(魅力型的统治)。
在依照章程进行统治的情况下,服从有合法章程的、事务的、非个人的制度和由它所确定的上司--根据他的指令的正式合法性和在他的指令的范围内服从他。在依据传统进行统治的情况下,在习惯的范围内,由于尊敬而服从传统所授命进行统治并受传统(在其范围内)约束的统治者个人。在魅力型统治情况下,服从具有魅力素质的领袖本人,在相信他的这种魅力的适用范围内,由于个人信赖默示、英雄主义和楷模榜样而服从他。
1.这种划分的适当性,只能由因此而在系统分类上所得的成绩加以证明。“魅力”(“天赋特质”)的概念是来自早期基督教的述语。对于基督教僧侣统治来说,首先是鲁道尔夫•索姆(1841-1917年,德国法律史学家)的《教会法》一书阐明了这个概念,尽管他不是根据这个术语进行论述。其他一些作者(例如卡尔•霍尔(1866-1926年,德国新教神学家、教会史家)的《狂热与忏悔的力量》[1898年版])[曾经]使某些重要的结论明朗化。因此,这个概念并不新鲜。
2.一般来说,下面首先要讨论的3种理想的类型,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真正以“纯粹”的形式出现过,这当然像平常一样,并不影响以尽可能纯粹的形式来确定概念。此外,次要将要讨论纯粹的魅力由于平凡化而引起的演变,并因此而大大地上升到靠拢经验的统治形式。然而,此时对于统治的任何经验的历史现象,下述论断都是适用的:统治一般“不是一部挖空心思杜撰出来的书”。而社会学的分类法给经验的历史研究工作仅仅提供了无论如何往往不可低估的优点:它在各种具体的情况下,可以对一种统治形式表示出是什么性质的,即什么是“魅力型的”,什么是“继承魅力型的什么是“职务魅力型的”,什么是“父权制的”,什么是“官僚体制的”,什么是“等级的”等等,或者什么接近这种类型,而且它也用勉强还算清楚的概念进行工作。在这里远远不可能认为,用下面阐述的概念模式,可能“囊括”历史上的整个现实。